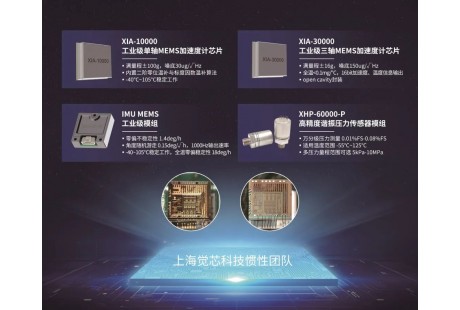硅谷的每個人都知道施樂在1970年代發明了現代計算機然而卻未能有效進行商業化的故事。但是當今硅谷最為成功的公司之一,Google母公司Alphabet,其無人車計劃似乎卻在重蹈施樂的覆轍。
1970年,施樂推出了自己的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PARC)。到1975年時,它的研究人員已經發明了帶圖形界面的個人計算機,這在當時幾乎領先了整整10年。不幸的是,這種技術的商業版直到1981年才發布,并且被證明是一次代價高昂的失敗。包括蘋果和微軟在內,太多的年輕公司都吸收了施樂的想法并最終統治了這個行業。
2009年推出的Google無人車計劃似乎也走上了一條類似的軌跡。到2015年10月時,Google對自己的技術已經有了十足的自信甚至讓一位盲人獨自在德州奧斯汀駕駛自己的車輛。
但就像40年前的施樂一樣,Google也在掙扎著把自己的技術帶向市場。2016年,項目改名為Waymo,原本預計要在2018年底推出無人駕駛商業服務。但是去年12月Waymo推出的服務既不是無人駕駛也幾乎算不上商用。每一輛車上還有一位安全司機,而且只面向幾百名客戶開放。
今天,有好些無人車初創企業正打算對Waymo做以前蘋果對施樂所做的事情。最近Nuro這家無人車初創企業就宣布獲得了9.4億美元的風投資金。另一家叫Voyage的,也正在美國最大的退休社區之一測試其無人車服務。
目前,這些公司的無人車服務還比不上Waymo的那么精致。他們的汽車最高時速只有25英里/小時。但蘋果一開始也是制造低端產品,然后再慢慢地向高端市場進攻,最后蠶食了施樂。如果Waymo戰略性不夠,像Nuro和Voyage這樣的公司也會對這家無人車技術先驅做同樣的事情。
Google的創始人,當然了,現在是Alphabet的CEO Larry Page,他很清楚施樂犯過的所有錯誤,并且決心要避免重蹈覆轍。2013年終接受《連線》雜志采訪時他曾經說過:“他們沒有把焦點放在商業化上。”根據The Information的Amir Efrati的說法,Page至少從2016年開始就一直督促Waymo進行商業化。
但是Page可能從施樂的經歷吸取到了錯誤的教訓。施樂的確嘗試過要對自己的技術進行商業化。只不過是沒有一項好的戰略去這么做罷了。尚不清楚Waymo是不是也是如此。
施樂浪費了巨大的技術優勢
早期的計算機由于價格太過昂貴而無法為一人專享。但1970年代早期時,施樂的研究人員意識到穩步下降的成本很快就會令個人計算在經濟上變得可行。而財力雄厚的施樂解放了它的研究人員,使得他們可以暫時忽略經濟約束,探索這些計算機未來的工作方式。
到了1975年,PARC已經制造出來一臺充滿未來主義風格的個人計算機,名字叫做Alto。這臺計算機具備位圖顯示,有一個鼠標,以及圖形用戶界面。施樂研究人員還開發了一款有著所見即所得界面的文字處理器。現在已成規范的操作,如“剪切”、“粘貼”以及“撤回”等都是由PARC的研究人員引領先驅的,而Alto還有著強大的聯網能力。
同樣在1975年,施樂還成立了一個新的系統開發部門來對PARC的計算機技術進行商業化。該團隊制訂了計劃來開發復雜的辦公信息化系統架構。每一位工人都將擁有一臺Alto式的工作站,里面配置了文字處理、電子郵件等辦公應用。還有一個快速的網絡將工作站連接到文件和打印服務器上。
1981年,隨著施樂8010辦公系統——也就是俗稱Star的引入,這一愿景變成了現實。這是一個技術奇跡,提供的能力遠超當時其他個人計算機上面的系統。
只有一個問題。這種工作站的售價為16595美元起——按照2019年的美元價格換算超過了45000美元。而一套實用的系統需要若干臺工作站以及文件和打印服務器,這么一套系統搭建下來輕輕松松就要好幾十萬美元。所以毫不奇怪,這套新系統賣得并不好。
蘋果采取了自底向上的辦法
當施樂的工程師正在開發Star的時候,一家很小的初創企業正在開發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個人計算機,這家公司的名字叫做蘋果。蘋果在1976年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款產品,666.66美元的計算機,Apple I。次年推出的Apple II是預安裝的,售價為1298美元(按當前價格計算為5300美元)。對于小公司來說這個價格已經足夠便宜,甚至個人都可以考慮入手一臺了。
很多計算專業人士對早期的像Apple II這樣的“微機”很不屑,認為這不過就是個玩具,但它們并不是一點用都沒有。關鍵突破發生在1979年,Dan Bricklin 和Bob Frankston在Apple II上推出了VisiCalc,這是全世界第一款電子表格程序。后來VisiCalc賣出了幾十萬份,從而幫助了Apple II成為企業客戶的一個有吸引力的選項。
同樣在1979年,蘋果跟施樂簽訂了一項轉折性的交易。前者在其備受期盼的IPO之前賦予了施樂對自己投資105萬美元的權利。作為交換,蘋果得以徹底考察了施樂隱藏在PARC的技術。在現已眾所周知的一系列會談中,PARC的工程師向一群蘋果工程師演示了Alto的先進能力,而后者則借此進行了詳細的記錄。
1983年,蘋果推出了第一臺圖形用戶界面的計算機Lisa,售價為9995美元(案今日價格為25000美元)。就像Star一樣,這款機器在商業上也失敗了。但跟施樂不一樣的是,蘋果迅速從自己起初的失敗中吸取了教訓。意識到價格高昂是客戶不愿買單的主因之后,蘋果在1984年推出了Macintosh。其建議價格為2495美元(相當于今天的6000美元),這個價格已經低到令其取得商業成功。
迅速搶占市場的案例
2011年Eric Ries出了一本很有影響力的書叫做《精益創業》,在書中他建議公司進入新市場時要開發“最小可行產品”——也就是最簡單的、足以吸引付費客戶的產品。這一策略使得公司可以開始向真正的客戶銷售真正的產品,并且獲得市場反饋,這個過程要盡可能地快。
Apple I計算機就是這種辦法的典型例子。這種計算機甚至只有一小群計算機愛好者才會組裝,而且能力遠遜當時市面上的其他計算機。但是另一方面這種東西又足夠簡單,簡單到幾個家伙在車庫就能組裝好。而且制造Apple I讓蘋果有了次年推出Apple II所需的經驗。而輕便的Apple II又反過來為VisiCalc這樣的軟件創造力市場,后者又進一步提升了對Apple II的需求。
等到蘋果在1983年引入Lisa的時候,該公司已經具備了超過6年的廉價個人計算機銷售經驗。這不僅幫助蘋果認清了Lisa的主要問題(太貴了),而且也讓蘋果獲得了迅速設計出一個價格更加可接受的版本所需的實踐知識和經驗。
相比之下,施樂對計算機業幾乎沒有什么經驗,對銷售低價個人計算機更是毫無經驗。所以當該公司的最初產品在1981年失敗時,就很難恢復元氣了。最終施樂設法推出了Star的廉價版,叫做6085。但那時候已經是1985年了,而且售價仍達4995美元——這個價格是Mac的2倍。
如何為無人車開發出一款最小可行產品
Waymo和施樂之間有些相似之處是很明顯的。就像施樂PARC一樣,Google的無人車項目也創造出來領先時代多年的技術。就像Alto一樣,Google的早期無人車也貴得離譜,據說高達25萬美元。
跟施樂一樣,Waymo也在努力實現自身技術的商用化。2017年11月,Waymo宣布自己已經在公路上開始全自動無人車的測試,并打算在2018年推出商用。
但Waymo沒有能實現自己的炒作。2018年12月,當Waymo推出其“商用”服務Waymo One時,每一輛車的方向盤后面仍然有一位安全司機。這幾乎意味著該公司逢開必虧——這大概也是Waymo只邀請了幾百人使用該服務的原因。
另一方面,個人計算機和無人。之間又有著明顯區別:一臺不怎么強大的個人計算機不會對誰構成威脅。顯然,如果會有生命危險的話,沒人應該匆忙將一臺廉價無人車投放市場。
但是開發最小可行產品的辦法不是只有一種。自治領域最困難的問題基本上都是在高速狀態下出現的。Waymo的車子在高速公路上并道以及在多車道高速公路左轉向時一直都有困難。高速意味著很長的剎車距離,這又需要昂貴的長程雷達。而且速度越快通常意味著安全性越低,因為在時速65邁的情況下發生碰撞致命的可能性要遠遠高于25邁的時候。
25邁的速度限制?
所以做無人車的最小可行產品的辦法之一可以是開發一款時速不超過25邁的汽車。對于Waymo想要建立的通用目的的地勢服務來說這個速度是不夠的。但是低速車輛的有用之處其實不難設想:比如機場擺渡車、包裹遞送、或者在受控環境(大學園區或者退休社區)下的的士服務等。
的確,Google在無人車項目的早年至少考慮過這些選項的其中一個。Lawrence Burns是一位汽車業的高管,自從Google無人車項目開始的時候他就一直給他們提供建議。在最近的一本書里,Burns提到了早期在商議商業化的時候他提出過“類似佛羅里達的退休社區那樣的大規模私人社區”是Google可以考慮的一個潛在市場。
不過最終Google并沒有采納這一想法。但是Google無人車項目的第一位領導Sebastian Thrun并沒有忘記這個。隨后Thrun繼續成立了在線學習服務Udacity,提供無人車編程的課程。幾年后,一些Udacity的員工決定利用自己傳授的技術創辦一家自己的無人車初創企業,這家企業的名字叫做Voyage。
在Autonocast播客最近的一集節目里面,Voyage CEO Oliver Cameron把這退休社區做無人車服務的點子歸功到Thrun身上。Cameron接受了這個主意然后開始去做。結果是:Voyage現在正在佛羅里達的The Villages測試無人車服務。那個地方是美國最大的退休社區之一。而無人車的最高時速正是25邁。
其他的無人車初創企業也在致力于開發低速服務。2016年,兩位工程師離開了Google無人車項目,成立了一家叫做Nuro的無人車初創企業(這是另一點跟施樂的類似之處:像Adobe和3Com這樣的公司都是由PARC工程師創辦了,因為他們對商業化的緩慢節奏感到沮喪)。Nuro也已經在利用小型全自動的無人車在鳳凰城送食品雜貨了。他們的競爭對手是Udely,這家無人車快遞初創企業宣稱沃爾瑪也是它的客戶。
自從2017年底以來,波士頓的初創企業Optimus Ride一直在波士頓Union Point的規劃社區運營者無人車接送服務。最近,該公司宣布又在哥倫比亞特區弗吉尼亞郊區的一個新的混合用途的住宅小區部署服務。Drive.ai也在達拉斯城區運營著類似的服務,而May Mobility則在3座不同的城市運營著低速無人駕駛通勤服務。
為什么撤除安全司機是關鍵
安全司機的成本至少跟常規的士司機的持平,此外無人車還需要昂貴的傳感器和計算機。鑒于Uber和Lyft實現盈利已經那么困難,帶安全司機的無人車服務幾乎鐵定是要虧錢的。
所以Waymo需要停止配置安全司機才能讓自己的服務在商業上變得可行。但首先,Waymo需要對自己的車可以安全地處理可能遇到的情況有信心才行。鑒于Waymo的車子鳳凰城周圍可能遭遇的各種情形,這是個巨大的挑戰。
在這方面Voyage及其他做低速服務的同行就有了一個巨大的優勢。它們不需要掌握在高速公路上匯入車流的技術,因為這些車本來就不上那種路。它們大部分都回避了高速交叉路口的問題,正是這一點給Waymo惹來很多麻煩。所以這些低速服務可能會比Waymo早一點撤除安全司機。
實際上,Nuro已經在朝著這一方向前進了;目前該公司正在使用兩款沒有給司機預留空間的車輛。目前,Nuro配置了有人駕駛的車輛跟在后面來保證安全。但Nuro的CEO ave Ferguson最近說他希望在下季度停止這種跟車的做法。
撤銷安全司機讓無人車公司可以從每一次出行中獲得盈利,這反過來讓快速擴張成為一種可能性。而當公司擴張時,它就有可能發現無數種令無人駕駛系統變得更安全更高效的小手段(包括技術上和管理上的)。開發者就會對客戶最關心哪些功能,哪些功能比較次要擁有更深入的了解。
最重要的是,隨著公司獲得越來越多的現實世界的經驗,并且積累越來越多的數據——它就能對如何在更高速度下安全行駛擁有新的洞察。如果最初的25邁服務有著卓越的安全記錄,并且得到了數百萬公里數據的支撐的話,公司就會有信心升級到30邁。而運營30邁服務所得到的數據又可以為35邁的服務打下基礎。如此不斷進步。
Waymo的商業化努力飄忽不定
以高速公路上的行駛速度來實現全自動無人駕駛,這一點對于任何這些初創企業來說多需要好些年的時間。Waymo的高管希望(也許是預期)能夠盡快完善自己的技術,把初創企業遠遠甩在身后。但我們有理由對這種想法提出質疑。
就像我之前提到過一樣,Waymo早在2015年10月的時候就完成了公路的第一次全自動無人駕駛。演示讓一位盲人在奧斯汀的街道上開車,這件事本身具備了一切引發公眾關注的媒體事件的特征。但奇怪的是,Google卻把它當作秘密保守了一年多。
這段時間正好是無人車項目領導從計算機科學家Chris Urmson轉到汽車也高管John Krafcik的過渡期。在奧斯汀演示結束后不久,Google放棄了用于演示的那款討人喜歡的2座“Firefly”——這種車沒有方向盤,最高時速為25邁,而是跟菲亞特克萊斯勒談判,使用傳統的Pacifica小貨車作為載具。
2017年初,Waymo開始走鳳凰城地區測試Pacifica。2017年11月,Waymo宣布將開始撤除駕駛座上的司機。Waymo甚至還給錢Jimmy Kimmel(編者注:美國脫口秀主持人)讓對方推銷Waymo的無人駕駛能力。Waymo承諾要在2018年底推出商用。再次地,該公司似乎開足馬力要推出無人駕駛商業服務。
但去年12月推出的Waymo One卻令人失望。這項服務在每輛車上面都有2名Waymo員工,距離無人駕駛差得太遠了。而且服務還不是面向公眾開放的,只有幾百名參與過Waymo原先測試計劃的人才能訪問。
Waymo在未來幾個月內用全自動無人駕駛服務來反擊質疑者的可能性當然也有。但Waymo的研發努力仍需要幾年時間也有可能。甚至Waymo當前的方法被證明走進了死胡同也有可能。我們不知道。而且Waymo的領導層似乎也不知道。
試點計劃不能取代商業發布
與此同時,一些初創企業可能最早今年就會推出全自動無人駕駛。然后,就像40年前的蘋果一樣,再慢慢向上蠶食更高速度的市場。如果Waymo進展太慢的話,一些初創企業競爭對手甚至可能會在Waymo之前推出無人駕駛的Uber競爭對手。
一個明顯的異議是Waymo通過Early Rider測試計劃獲得了顯著的現實世界經驗。這項計劃給選定的幾百名鳳凰城居民試乘Waymo車輛的機會,從很多放哪敢嗎來說都類似于真正的商業服務。在測試計劃中,乘坐的都是真實的客戶,行駛的也是實際的路線,很多情況下他們還要付費——盡管費用大概不能包住真正的成本。這種獲取現實世界經驗的辦法代價高昂,但是你可能會認為Waymo可以從這類試點計劃中獲得跟真正運營商業服務時可得到的一樣的客戶反饋。
但這種看法是錯的。試點計劃不能取代實際的商業產品,施樂交了很多學費才知道這一點。
雖然施樂直到1981年才披露其完整的商用產品,但1970年代末時已經讓部分Alto曝光給外界了。從1978年開始,Alto就被送到學術、商業以及政府界的潛在客戶,甚至有幾臺還送到了白宮。
施樂的研究人員大概拿到了有價值的用戶反饋來幫助進一步完善Alto的用戶界面。但這些市場調查并不能幫助施樂回答這個最根本的問題:Alto的吸引力是否足以讓施樂賣出很多大賺一筆?任何技術光靠新穎性賣出幾十個單位是沒有問題的。但這并不能幫助施樂找到如何將Alto變成可行商業產品的辦法。
Waymo的Early Rider計劃是個干擾
Google在這10年的早期做Google Glass的時候也犯過類似的錯誤。他們沒有發布實際的商用產品,而是推出了Explorers Edition,早期采用者支付1500美元才能體驗這種技術的半成品。
再次地,Explorer計劃也許為Google工程師提供了有價值的用戶接口反饋。但無助于Google找到如何做出普通客戶原因購買的Glass的辦法。實際上,對于這個問題Google從來都沒有找到一個非常令人信服的答案。Google最終轉型為將Glass賣給工廠車間使用,但這項技術顯然已經遠遠落后于早期的期望。
Waymo的Early Rider計劃也掉進了同一個坑(帶安全司機,客戶只有受邀的Waymo One最好把它解讀成Early Rider計劃的延續)。對于像Waymo這樣雄心勃勃的項目來說,工程師要解決的問題幾乎是無窮的。推出實際商用服務有助于找到這些問題的輕重緩急。
一旦公司有了真正的付費客戶,就有可能發現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可能只有1、2個,想要的功能主要也就1、2個。可能有些問題對服務成本或者對某些阻止服務擴張的瓶頸的影響不成比例。
關鍵是,開發者會發現很多種發布前看起來似乎重要的挑戰實際上并不是。他們會發現一些工程師做的功能其實幾乎沒人用。他們會發現別人在攻關的復雜昂貴的解決方案所針對的問題在現實世界中是很罕見的。當客戶的需求變得更加清晰之后,一些項目甚至被證明是毫無必要也說不定。管理層就可以將這些項目擱置,把工程師重新分配到解決更加迫切的客戶需求的項目上。
這種學習很少能在類似Waymo的Early Rider計劃這樣的試點計劃上取得,因為沒人知道最終的商業版跟試點版的相似性有多大。主流客戶關心的問題可能跟早期采用者不一樣。規模運營服務也許會暴露出一些在小型測試中不明顯的問題。了解了問題之后,公司就必須同時去處理許多不同的問題。這樣導致任何以惡搞問題要想取得快速進展都很難。
施樂用了6年的時間來完善Star功能,可到頭來卻發現這一切都無關緊要了,因為產品太貴了。把一個功能受限的產品迅速推向市場本來可以讓施樂明確橫亙在自己和商業成功之間的真正因素是什么——高價格才是他們要解決的問題。
這個對于Waymo來說似乎也是一樣。該公司在尋找無人駕駛的地勢服務應該如何運作的問題上已經投入了數百萬美元。但如果可在城市范圍內運營的的士服務所需的技術還需要5到10年時間才能就緒的話該怎么辦?那樣的話Waymo就不僅在不必要的工作上浪費了數百萬美元,而且還干擾了自己的工程師去推出一項野心沒那么大的服務。從一項抱負小一點的服務開始也許才是實現城市級的士服務最快捷的道路。
“他們一直在做這些登月項目”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大量借鑒了《Dealers of Lightning(創新未酬)》這本書的內容,這是Michael Hiltzik 1999年出版的反映1970年代施樂PARC歷史的經典之作。
在本書中,Hiltzik指出施樂的一些內部人士曾經督促過公司采取蘋果類似的策略。1976年,一位名為Robert Spinrad的主管向自己的老板建議公司先從面向書記員市場推出一款簡單低價的PARC技術產品。
1990年代時他告訴Hiltzik說:“我的看法是我們可以從小做起發展上去。但是每次都得不到采納。那個時代的施樂除了全面產品開發絕對不會考慮第二選項。”
Hiltzik寫道,問題在于“施樂總部對產品開發計劃的預期是起碼要達到一定的體量。”或者就像一位施樂的資深人士總結那樣:“施樂很難理解規模不到一億美元的任何東西。”
在讀完這本書之后,我問Hiltzik是否認為Waymo會重蹈覆轍。但Hiltzik對Waymo的機會感到樂觀。
Hiltzik認為“Google不那么(像施樂那樣)死綁在單一的商業模式上。”他說施樂高管“其實是想讓PARC想出一些發明辦公設備的新手段”——最好是像施樂出租復印機那樣可以出租出去的辦公設備。
Hiltzik說:“我認為Alphabet的方向有點不一樣。”他認為Google的產品組合更廣,對于每一種技術該采用哪一種商業模式也更在行。
“完全正確”
但是Eric Ries不同意。他在接受電話采訪時告訴我說:“我認為你的類比完全正確。”
Ries說,Google“從來都沒有掌握如何在非臨近領域建立新業務類別的經驗。他們不斷地做這些登月項目,把全世界最聰明的人都招至麾下,給他們無限的資源,然后再將其轉為商業產品時就撞上了絆腳石。
Alphabet的主管愿意把自己看成是有別于施樂那幫裝模作樣、官僚做派的人,但這種區別有多大其實并不清楚。就像任何一家大公司一樣,Alphabet也喜歡追逐大市場。就像Voyage CEO Oliver Cameron在Autonocast概括那樣,像Google這么大的公司如果一開始把炒作得那么厲害的技術用來為退休社區提供的士服務的話,“可能會被人笑話。”
施樂高管認為,開發出一套大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辦公計算系統是追逐大市場的手段。但現在回想起來,我們知道他們是錯的。做大的最好辦法往往是從小做起。